万历天幕下的浮沉宝藏文最新章节列表_万历天幕下的浮沉宝藏文全文免费阅读(徐光启张文明李贽)
2025-08-14 17:18:53 编辑:蝶霜飞
《万历天幕下的浮沉》 小说介绍
男女主角分别是徐光启张文明李贽小说名字《万历天幕下的浮沉》,由作者“寿南峰的雷克塔”创作,故事情节紧凑,引人入胜,本站无广告干扰,欢迎阅读!更新时间2025-08-14,目前在【最新热门小说推荐网站 - 橙子吧】上可阅读。
《万历天幕下的浮沉》 万历天幕下的浮沉精选章节 免费试读
万历六年四月初二,江陵县卫所的校场突然热闹起来。数百个穿着褪色军甲的汉子聚在演武台前,手里攥着生锈的刀枪,为首的是个独眼老将,腰间挂着块"昭武校尉"的腰牌——正是荆州卫左所的千户王承祖。
徐光启赶到时,王承祖正用脚踹着卫所的辕门,声如洪钟:"把张文明那狗贼交出来!不然老子拆了你们布政司!"
赵勇带着衙役们挡在门前,手里的水火棍握得死紧:"王千户,朝廷有法度,不可乱来!"
"法度?"王承祖冷笑一声,指着身后的军户们,"我这些弟兄戍守荆襄三十年,九死一生,换来的军屯田被姓张的占了大半!这就是你们说的法度?"
徐光启挤过人群,见军户们个个面黄肌瘦,甲胄上的补丁比铜钱还多,心里咯噔一下。他前日核查军屯田时,发现被侵占的四十五亩地全在左所辖区,当时还纳闷卫所为何毫无动静,原来是在攒着劲闹事。
"王千户稍安勿躁。"徐光启拱手道,"张文明已被收押,所侵占的军屯田正在清点,不出三日必定归还。"
"归还?"王承祖眯起独眼,"说得轻巧!去年秋收,我左所三百军户,竟有半数没领到粮饷,就是因为田被占了!有个叫李二狗的小兵,家里五口人饿死了三个,你赔得起吗?"
这话像重锤砸在徐光启心上。他在苏州见过军户,虽也清苦,却从未到这般境地。荆州卫是防备荆襄流民的重镇,军户若是哗变,后果不堪设想。
"千户说的李二狗,是否住在卫所西巷?"徐光启突然想起什么,"昨日我去核查军户名册,见他家登记着'阖家病故'。"
王承祖脸色一沉:"病故?那是饿死的!他娘为了给娃换口粮,把自己卖去了青楼,到现在都没消息!"
人群里爆发出呜咽声。一个瘸腿军户哭喊道:"俺们守着长江防线,倭寇来的时候冲在最前面,现在连口饭都吃不上...这兵没法当了!"
徐光启喉头发紧,转身对赵勇道:"去账房支二十石米,先给军户们应急。"
"先生!"赵勇急了,"布政司的存粮是预备赈灾的,动不得啊!"
"出了事我担着。"徐光启语气斩钉截铁,"军户们要是饿出乱子,赈灾粮再多也没用。"
等赵勇领着衙役们运米来时,军户们的情绪果然缓和了些。王承祖虽仍绷着脸,却没再踹门,只是盯着徐光启:"米我们领了,但地要是交不出来,老子照样拆衙门。"
"我随千户去军屯看看。"徐光启解下腰间的铜令牌,"现在就去。"
军屯在卫所西南的沙洲上,一片荒滩被开垦成梯田,只是田埂大多塌了,好些地块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。王承祖指着靠江的一片熟地:"那三十亩就是被张文明占的,他让人挖了条渠,把江水引过来种水稻,害得我们下游的旱地全成了盐碱地。"
徐光启蹲下身,抓起一把土,果然又咸又硬。他想起《鱼鳞图册》上标注这里是"上等水田",想必是被盐碱化后才被弃置,却被张文明巧取豪夺,改造成自家的稻田。
"张文明怎么敢动军屯田?"徐光启不解。军户土地属卫所管辖,地方官无权处置,这是太祖定下的规矩。
王承祖往地上啐了口唾沫:"他勾结了卫所的经历司!那个姓刘的经历,收了张家二百两银子,就把地契改成'无主荒地',明目张胆地送给他小舅子!"
徐光启心里一凛。经历司是卫所的文书机构,掌管军户名册和田契,若是他们徇私枉法,军屯的土地确实能被轻易侵占。他想起李贽说过,张居正改革时曾想整顿卫所,却因阻力太大而搁置,看来这军屯里的猫腻,比地方上的隐田还要复杂。
"刘经历现在何处?"
"早被张文明送走了,说是去武昌府'任职',其实就是跑路。"王承祖冷笑,"我派人去追,却被府衙的人拦了回来,说没有布政司的文书,不得擅动朝廷命官。"
徐光启掏出纸笔,飞快地写了份文书,盖上随身的铜印:"拿着这个去追,就说是我下令的。若有人阻拦,以'通匪'论处。"
王承祖接过文书,独眼亮了起来:"好小子,有种!不像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文官。"他突然扯开衣襟,露出胸口一道狰狞的伤疤,"嘉靖四十一年,我在台州抗倭,被倭寇的倭刀划开的,当时肠子都流出来了,就想着能活着回来种好那几亩军屯田...没想到啊..."
后面的话他没说,只是抹了把脸。徐光启看着那道伤疤,突然想起去年在泉州见到的戚家军士兵,他们的铠甲上也有类似的伤痕,只是那些人眼神里有光,而眼前的军户们,眼里只剩麻木。
"千户放心,"徐光启郑重道,"不仅要还你们土地,还要查清粮饷被克扣的事。"
回到卫所时,钱六正蹲在墙角和个老军户说话。见徐光启回来,他连忙起身:"先生,这老爷子知道刘经历的底细!说他去年卖军粮给盐商,赚了不少黑心钱。"
老军户颤巍巍地掏出个布包,里面是几张发霉的粮票:"这是去年的领粮凭证,上面写着'上等米',实际发的全是陈米,还有不少沙子..."
徐光启拿起粮票,上面盖着荆州卫和江陵县的双印,显然是官商勾结的铁证。他突然明白,张文明敢动军屯田,不仅是仗着张居正的势,更是因为卫所内部早已烂透,从上到下都在蚕食军户的血汗。
"先生,"钱六压低声音,"刚才李参议派人来,说京城来了位御史,明日就到江陵,说是要查'新政扰民'的事。"
徐光启心里一沉。御史查案本是常事,可偏偏在这时候来,多半是冲着张文明的案子。张居正虽批复"从严处置",但朝中反对他的人不少,保不齐会借题发挥,把矛头指向改革。
"知道是哪位御史吗?"
"听说是湖广道的刘台。"
徐光启倒吸一口凉气。刘台是张居正的门生,却因反对考成法而与恩师反目,去年刚被贬为湖广道御史,此人最是擅长借题发挥,若是被他抓住把柄,别说归还军屯田,恐怕连李贽都要受牵连。
"必须在刘御史到之前,把军屯的案子结了。"徐光启当机立断,"钱六,你去查刘经历的下落,务必今日找到;赵勇,你带衙役去张文明小舅子家,把那三十亩稻田收回来,不管他愿不愿意。"
两人领命而去,徐光启则赶回布政司向李贽禀报。老参议正对着一份卷宗发愁,见他进来,把卷宗推了过来:"你自己看吧,刘台的弹劾奏章草稿,已经送到武昌府了。"
徐光启翻开一看,上面写着"江陵小吏徐光启,借丈量土地之名,煽动军户哗变,意图动摇国本",后面还附了几张"乡民控诉"的状纸,字迹竟与周显谟的账房先生如出一辙。
"这是栽赃陷害!"徐光启气得手发抖,"他们连军户的苦难都要利用!"
"意料之中。"李贽倒很平静,"刘台恨首辅入骨,早就想找个由头攻讦新政。张文明的案子,不过是他递刀子的机会。"他敲了敲案几,"现在有两条路:一是把你交出去顶罪,平息风波;二是把军屯案查透,拿出铁证,让刘台无话可说。"
"学生选第二条。"徐光启毫不犹豫,"若是退缩,对不起那些饿死的军户,也对不起首辅推行新政的初心。"
李贽看着他,突然笑了:"老夫没看错人。你记住,对付这种罗织罪名的小人,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真相摆在太阳底下。"他从抽屉里拿出个木盒,"这是当年我在兵部当主事时,查抄的军屯旧档,里面有宣德年间的军户名册,或许能用上。"
徐光启打开木盒,里面是几本线装册子,纸页泛黄发脆,上面用小楷记录着每块军屯田的位置、产量,甚至连耕种的军户姓名都清清楚楚。他翻到荆州卫左所那一页,只见"李二狗"的曾祖父"李老实"的名字赫然在列,名下正是被侵占的三亩水田。
"有了这个,谁也别想抵赖。"徐光启握紧册子,指尖因用力而发白。
傍晚时分,钱六终于回来了,身后跟着两个衙役,押着个五花大绑的胖子——正是刘经历。那胖子瘫在地上,肥硕的脸上满是鼻涕眼泪:"徐先生饶命!都是张文明逼我的!他说要是不照做,就把我贪墨军粮的事捅出去..."
"贪墨军粮多少?"徐光启厉声问道。
"去年...去年冬天,卖了三百石上等米,换了...换了五十两银子..."
人群里的军户们顿时炸了锅,若不是赵勇拦着,差点冲上来把刘经历撕碎。王承祖一脚踩在胖子脸上:"老子就说粮饷怎么少了!原来是被你这狗东西贪了!"
徐光启示意衙役把刘经历拖下去,转身对军户们道:"刘经历的罪证已经查实,明日就押往武昌府问斩。被侵占的军屯田,今夜就组织人手收割,粮食全部分给军户!"
军户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,有几个老兵当场就哭了,跪在地上给徐光启磕头。徐光启连忙扶起他们,心里却沉甸甸的——这些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,竟要靠拼命争取才能拿回,这世道实在太不公。
深夜的军屯里,火把连成了长龙。军户们挥着镰刀收割水稻,孩子们提着篮子捡拾掉落的谷粒,连王承祖都扛着个麻袋,一瘸一拐地来回搬运。徐光启站在田埂上,看着这热闹又心酸的场景,突然想起李贽说的"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"——百姓所求,不过是温饱二字,可这最简单的愿望,却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。
"先生,"赵勇拿着个陶罐走过来,"这是军户们熬的米粥,您尝尝。"
编辑推荐
 雪花只开在冬天作者:大神类型:现代言情
雪花只开在冬天作者:大神类型:现代言情 她的星辰大海作者:某君类型:青春校园
她的星辰大海作者:某君类型:青春校园 春风十里,贺卿良辰作者:ABC类型:现代言情
春风十里,贺卿良辰作者:ABC类型:现代言情 青鸟飞过荆棘岛作者:匿名类型:军事历史
青鸟飞过荆棘岛作者:匿名类型:军事历史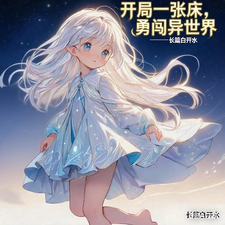 开局一张床,勇闯异世界作者:长篇白开水类型:玄幻修仙
开局一张床,勇闯异世界作者:长篇白开水类型:玄幻修仙
 万历天幕下的浮沉
万历天幕下的浮沉 山海攀高
山海攀高 轻城一顾终别离
轻城一顾终别离 半分交换
半分交换 三杯,敬自己
三杯,敬自己 雪覆新坟叠旧坟
雪覆新坟叠旧坟 花钱带全家出去玩
花钱带全家出去玩 崔嘉宁裴澈安
崔嘉宁裴澈安 乔念舒陆澈安
乔念舒陆澈安 冉溶月裴时焕
冉溶月裴时焕 夏书澜陈屿洺
夏书澜陈屿洺 小丑的献礼
小丑的献礼